以下是对原文的润色:
当女性掌握话语权,男性开始感到恐惧
当年,文学界曾发生一起引人瞩目的公案:张洁,这位两度荣获茅盾文学奖的女作家,在创作一部八十万字的小说《无字》时,遭遇了王蒙的严厉批评。王蒙指出,张洁在书中滥用话语权,将男性角色描绘得过于不堪。对此,我有着自己的见解。
在中国文坛,王蒙无疑是一位重要人物,他的《青春万岁》和《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都受到了广泛的赞誉。然而,张洁作为一位专职作家,她的作品更贴近真实,更具个性。在我看来,王蒙更像是一位文化官员,而张洁才是真正的女性作家。
张洁的作品是小说,虽然其中的人物有其原型,但王蒙却对此进行过度解读,甚至将其视为对男性的仇恨。他试图用“节操”、“文德”和“文格”等概念来压制女性作家,这不过是掩盖自己内心的偏见与私心。
王蒙早已习惯于男权话语体系,他对女性的处境缺乏直观的感受。他所塑造的女性形象几乎都被描绘成男性理想的对象,充满了“从属感”。她们很难成为主角,只是被男性作家观察、临摹和描绘的对象。无论是陈忠实、路遥、余华、刘恒、张贤亮、王小波、贾平凹还是其他男作家,他们笔下的女性大致分为两类:一种是圣母,为所爱之人奉献一切;另一种是荡妇,自我放逐和堕落。
张洁的《无字》则是一部从纯女性视角出发的小说,主角也是女性。书中的男性角色被描绘得一个比一个糟糕,而女性则展现出坚韧与贱气。这种贱气,有时也是男性太渣造成的。女性对男性的爱恨交织在书中得到了真实的展现。张洁之所以写这样的书,实际上是对男性群体的冒犯,直接让男作家们感到不安。
女性长期处于社会的最底层,她们的声音往往被忽视和压制。而张洁仅仅是从女性的角度写了几个自私的男性,就让男作家们感到不适应,他们试图用传统的评判标准来打压女性作家。但实际上,他们在自己的作品中塑造的女性形象还少吗?女性在他们的作品中,要么被赞美,要么被同情,但基本上只是作为帮助男主角探索情感世界或实现人生理想的“道具”,从未摆脱过“角色的从属性”。他们在描写这些女性角色时,又何曾考虑过哪些可写、哪些不可写的“节操”和“文格”?
我觉得王蒙对张洁的批评,只是因为他已经习惯了站在男性的视角,以法官自居,要求别人只能发表“一面之词”。他们害怕一旦解释情事的话语权被女性掌握,他们便无法再随心所欲地伪装自己的道貌岸然。
曾经,我也听到过有人评价我的文章,说“从你的文风来看,真不像是女人写的,这点很难得”。对此,我深感疑惑,为何“不像女人写的”就“很难得”?难道“像女人写的”就低人一等吗?这恰恰反映了我们的社会已经习惯了由男性作家占据写作领域的话语权,并因此形成了一系列评判标准。
我认为,女性的视角和表达方式,可以与男性完全不同,我们的文风也可以自成一格,不必刻意模仿男性的写作手法、遵循他们制定的写作规则和视角。正因为这样,一部分男性对我深恶痛绝,尤其是那些骨子里丝毫没有“男女平等”意识的男性。他们总是因为我写文章批评出轨男、直男癌而对我进行人身攻击。
我并不会因此感到郁闷,因为我知道,那些讨厌我的男性,我拉黑的人中90%都是男性。但我有志同道合的女性读者就足够了。我为何要迎合那些讨厌我的男性?这不是有病吗?
如果一个人因为看了别人的文艺作品而感到被冒犯,那么很可能并不是文艺作品的问题,而是那个人内心的小九九被发现了。他们无法面对自己,才会通过攻击别人的方式,来保全自己最后的颜面和自恋。
我想,当女性真正掌握话语权,那些习惯了男性话语体系的男性,可能会感到恐惧和不安。因为一旦女性也开始发声,他们便无法再随心所欲地维护自己的假象。这将是文学界的一次重大变革,也是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
作者:晏凌羊,一位情感专栏作者,新女性主义作者,中国作协会员。她的作品涉及情感、社会、文化等多个领域,深受读者喜爱。她不仅拥有丰富的文学素养,还拥有金融从业经验,现为广州某文化信息咨询公司创始人、某文化传媒公司联合创始人。欢迎关注她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与她一起探讨文学、情感和社会的多个层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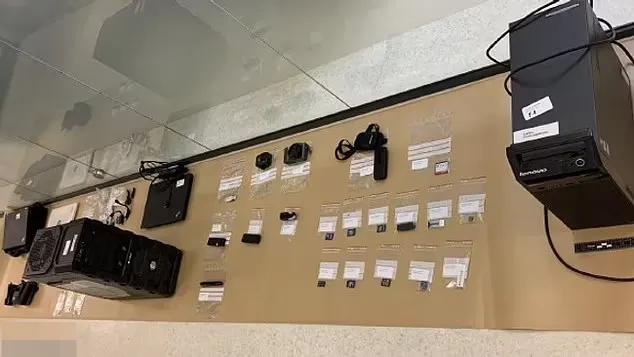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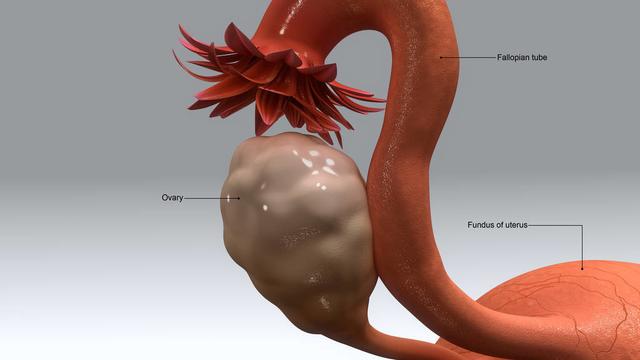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11000000000001号
京公网安备11000000000001号